因为疫情,欧洲哲学家们吵翻了!
导读:在这场论战中,哲学家们关心的是欧洲的疫情到底有多严重?各国政府的防疫措施是过于严厉还是过于宽松?疫情过后,欧洲还能够恢复往日的样貌吗?疫情还在酝酿着一种尚不可捉摸的政治后果?

78岁高龄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迎来了他人生的“至暗时刻”。
这不仅是因为意大利在短短一个多月内,成为了整个欧洲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国家,而这种疾病对于65岁以上的老人来说有可能是致命的。更重要的是,阿甘本处在了欧洲哲学界近年来最大的一场论战的中心。
阿甘本在哲学界的地位备受尊敬,但他对疫情的思考却引发了几乎整个欧洲哲学界的反对,即便是其朋友也难以认同。
在这场论战中,哲学家们关心的是欧洲的疫情到底有多严重?各国政府的防疫措施是过于严厉还是过于宽松?疫情过后,欧洲还能够恢复往日的样貌吗?疫情还在酝酿着一种尚不可捉摸的政治后果?

吉奥乔·阿甘本,意大利哲学家,意大利维罗拉大学美学教授,并于巴黎国际哲学学院教授哲学
无端的“紧急状态”
自从1月31日罗马出现首2例新冠肺炎病例,意大利政府就宣布进入为期半年的“国家紧急状态”,并暂停了所有往返意大利和中国大陆及港澳台的航班。在此后的20天里,意大利境内仅新增了1例本国籍病患。
好景不长,2月21日后,北部伦巴第大区突现社区传播,确诊病例猛增,甚至在第二天就出现首例死亡病例。
显然,“国家紧急状态”已经不足以应付疫情的突袭。意大利政府在2月22日宣布对密集出现疫情的北部伦巴第、威尼托两大区11城镇的约5万居民实行隔离检疫,并在该区域内实施了多项管制措施,包括禁止公众集会,取消一切体育、宗教活动,关闭学校、酒吧等。此后,官方还增派了警察在隔离区巡逻,并派遣军队介入隔离区的检查站。
论战的导火索是2月25日,阿甘本在《宣言报》和“任意”出版社的博客上刊登的一篇社论,题为《由无端的紧急状态带来的例外状态》。但让老哲学家感到担忧的,并不是疫情的蔓延,而是意大利政府采取的强硬防疫措施。

阿甘本在《宣言报》刊登的《由无端的紧急状态带来的例外状态》一文
阿甘本指责意大利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疯狂、不合理且毫无依据的”,因为意大利国家研究中心的声明显示出,疫情并未像媒体和政府官方渲染的那么可怕。
在阿甘本看来,政府以“卫生与公共安全”为名的法令条款“模糊且不确定”,却会让悬置法律效力的“例外状态”合理扩散到意大利所有大区。他更担心当人们习惯了恐惧,这种恐惧会转换为一种对安全的渴望,人们会为了满足这种渴望自愿放弃个人自由。
也许是因为阿甘本发表这篇社论之时,欧洲疫情的严重程度的确尚不明朗,阿甘本的判断是否正确也无从知晓。
实际上,在意大利,并不只有阿甘本对政府的严厉措施怀有抵触情绪。政府重启“国家紧急状态”,无疑令意大利人苦涩地回忆起1970年代当局为镇压“红色旅”等极左团体动用“莫罗法”制造的“白色恐怖”。
两天之后的2月27日,阿甘本的“老朋友”、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首先发难,他在“二律背反”网站上发表题为《病毒性例外》的简短回应文章。论战的序幕拉开。

让-吕克·南希在“二律背反”网站上发表的题为《病毒性例外》一文
身处法国的南希也许感受到了疫情的紧迫。就在这一天,法国的疫情迎来了第一个高峰,当日新增20例确诊病例。南希提醒“老朋友”注意,我们有疫苗应对“常规”流感,但是还没有疫苗可以对抗新冠病毒。这个差别会使得冠状病毒有更高的致死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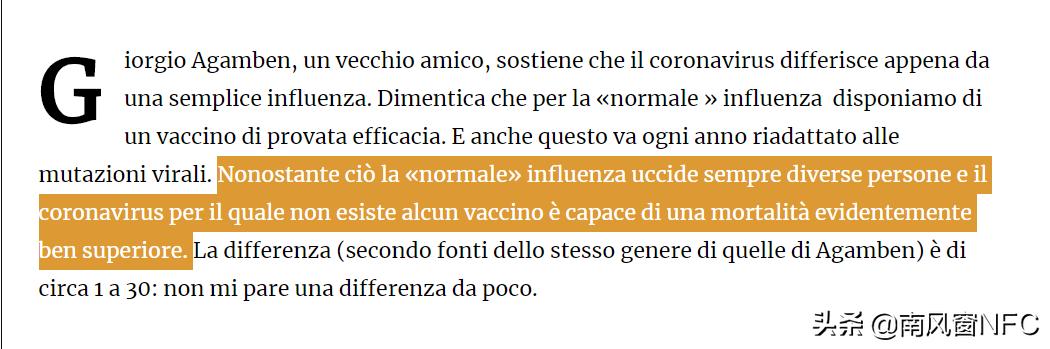
《病毒性例外》文中所述:“正常”流感尚会使人致命,而没有疫苗的冠状病毒的死亡率显然要高得多
至于“例外状态”,南希则认为不能仅仅归咎于意大利政府,因为“这种例外实际上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成了一种规则”。换句话说,真正有益的政治反思应当把矛头指向全球化,而“政府只是可悲的执行者”。

《病毒性例外》文中所述:政府不过是可悲的执行者
事实上,据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的防疫并非如铁桶一般,而是漏洞百出,造成了一种“封锁归封锁,活动归活动”的态势。
对哲学家马西莫·卡奇亚里而言,真正的“例外”是这种完全混乱的氛围。他在27日接受《新普利亚日报》的访问时感叹:“如果俱乐部照常开放,那么,在没有新冠病毒染病记录的地区封闭学校的意义何在?”

马西莫·卡奇亚里,意大利哲学家,先后任教于威尼斯建筑大学和圣拉斐尔生命健康大学
与阿甘本对政府限制自由的担忧形成鲜明反差,卡奇亚里抱怨政府“脆弱且无脑”,只能被动遵循孤立主义的逻辑。
3月1日,意大利政府和议会通过了《防控新冠疫情法令》,将意大利分为“红区”、“黄区”和安全区。3月4日,意大利首次出现单日死亡病例过百。
与此同时,阿甘本的文章引发的争议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哲学家加入到批判阿甘本的行列。“二律背反”网站则成为了学者们论辩的主战场。

(”二律背反“网站。“二律背反”是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提出的哲学基本概念,指双方各自依据普遍承认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公认为正确的两个命题之间的矛盾冲突)
创办《欧洲精神分析期刊》的意大利哲学家塞吉奥·本维努托3月5日发表文章,题为《欢迎来隔离》。(他拿自己的名字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因为在意大利文中,本维努托的意思就是“欢迎”。)
虽然本努韦托把阿甘本称作“我最喜欢的哲学家之一”,但是他并不认同阿甘本。他认为,阿甘本把政府采取的措施看成是“统治阶级暴虐本能”的结果的观点既不切实际,也容易助长阴谋论。
而且,人们面对未知病毒的恐慌并不是“非理性的”。在当前,政治权力选择制造恐慌,以鼓励人们隔离病毒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3月8日,来自印度的两位年轻哲学家沙吉·莫汉与迪维亚·德维迪也向阿甘本宣战。
两人发表《被遗弃者的共同体:回应阿甘本与南希》,大致认同南希的反驳。他们认为,与“例外状态”相对的“普通状态”只存在于阿甘本的想象中。比如在印度就不存在处在普通状态的人,几乎所有人都因属于特定种姓而可以称作是“例外”的。
此时疫情已急转直下,包括米兰、威尼斯、帕尔马等在内的11座城市,被意大利政府宣布“处于隔离检疫的警戒状态”,而意大利单日新增确诊数却还是突破了1500例,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万。
总理孔特在3月10日凌晨签署全境防疫法令,使得意大利成为全球首个为应对新冠疫情,在全国范围实施封闭政策的国家。
但是阿甘本并未动摇。他在意大利封国的第二天3月11日发表题为《论感染》的文章再次申明立场,想要揭示“传染”这个医学概念的生命政治学意涵。
阿甘本引用了曼佐尼描述1630年代米兰大瘟疫的小说《约婚夫妇》,谴责意大利政府的措施“实际上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潜在的涂油者”。他担忧这些防疫措施有可能导致的“人际关系的恶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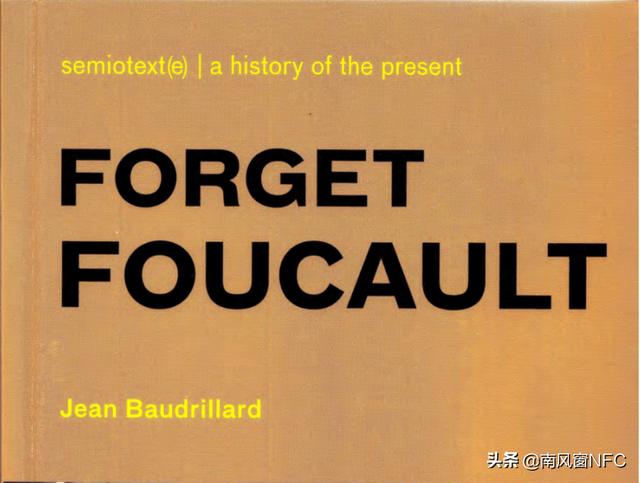
(《约婚夫妇》是意大利十八世纪著名作家曼佐尼代表作,其地位在意大利文学史上仅次于但丁的《神曲》、彼特拉克的《抒情诗集》和薄伽丘的《十日谈》,是一部以平民为主人公的长篇历史小说)
哲学家洛可·隆奇在14日发表的《病毒的美德》中对防疫措施做了与阿甘本截然相反的解读。与人保持距离并不是对自由的限制,因为真正的自由是“在特定情况下做必须做的事情”。隆奇也不像南希那样认为今天只存在“例外”,而是根本不存在“例外”。
“病毒显示出,整体必然包含在部分中,而在自然中没有任何自治的领域可以构成‘例外’。”有些人面对疫情蔓延而不愿有所行动,正是因为他们愚蠢地相信自己的“例外”。
真正让阿甘本备受打击的,是哲学家兼记者保罗·弗洛雷斯·达凯斯在《微型巨人》杂志发表的文章。
这篇于3月16日刊出的文章《哲学与病毒:阿甘本的幻觉》言辞尖锐,达凯斯显然没有阿甘本的朋友和崇拜者那么客气。他嘲讽阿甘本“偏爱迷信的传播与神学的反刍,偏爱精神上的娱乐和反科学的驱魔,偏爱平庸的抱怨和自恋的妄想”。
因为阿甘本的文章“旨在证明并没有传染病,而只有传染观念的传播”。达凯斯断言,阿甘本提供的是一种“糟糕的哲学”,在逻辑手册上需要添加上“阿甘本的失败”。
达凯斯的言辞彻底惹恼了阿甘本。老哲学家在第二天17日发布声明:“一位意大利记者此前发挥自己的职业优势,误解和扭曲了我对一些伦理学困惑的反思”。但声明的大部分内容,只不过重复了他在前两篇文章中的观点。
显然,阿甘本并没有要修正自己的观点的意思。他只是要强调自己担忧的不只是当下,还有瘟疫结束之后,我们该如何共同生活。
不过,形势已经对阿甘本极为不利。本努韦托直接把第二篇文章定名为《忘记阿甘本》。他无疑是模仿了43年前法国学者让·鲍德里亚批评福柯的文章《忘记福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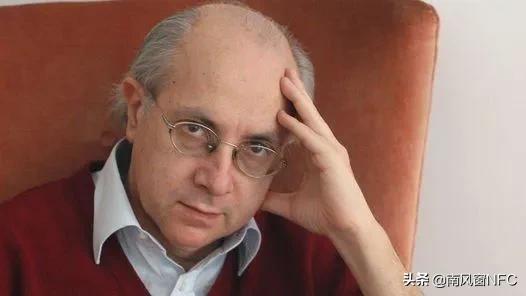
阿甘本的另一位“老朋友”、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伊·齐泽克也在《温情脉脉的野蛮行径乃是我们的宿命?》中表明,“虽然对阿甘本充满敬意,但我不同意他的见解”。他认为,保持身体上的距离是出于对对方的尊重,而不一定会“把人们分割开来”。
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非常坦然地承认了这一点。
埃斯波西托与南希:“生命政治”之争
唯一站出来为阿甘本辩护的是哲学家罗贝托·埃斯波西托。

罗贝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意大利哲学家
2月28日,他为《共和报》和“二律背反”网站各写了一篇文章,分别题为《党派与病毒:生命政治当权》和《“治”到最后》,主要是为了回应让-吕克·南希。
实际上,埃斯波西托和阿甘本的哲学工作有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生命政治”。它成了这次论战的另一个焦点。
“生命政治”的概念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的,指涉18世纪西方社会出现的一种将人民当作生物性人口加以计算和调节的治理技术。这种治理技术结合了人口学、统计学、公共卫生和都市计划等新兴知识,政治权力从此不再通过死亡的威吓施展,而是专注于养育国家的人口素质。
阿甘本在福柯的基础上提出了“神圣人”和“赤裸生命”的概念,用来表示“例外状态”下被政治弃置的人的处境。埃斯波西托则敏锐地意识到,南希对阿甘本观点的疑虑源自于他对“生命政治”概念由来已久的怀疑态度。
埃斯波西托认为,“生命政治”在现代社会的应用有目共睹,而南希所使用的“病毒性”一词本身就表明生命政治的污染跨越了政治、社会、医疗和技术多种语言。

罗贝托·埃斯波西托在“二律背反”网站上发表的题为《“治”到最后》一文
埃斯波西托同意阿甘本,虽然长时间以来,紧急法令都被用以应对疫情,但却“并非绝对必要”。将政治推向例外状态,终究会损坏民主国家所珍视的权力平衡。
不过,埃斯波西托的观点要更为折中。他也像卡奇亚里一样意识到,当下意大利政府表现出的与其说是极权主义,不如说是“公共机构的崩溃”。
在阿甘本发布《声明》的同一天3月17日,让-吕克·南希再次出手。这次他直接表达了他对“生命政治”及其狭隘视野的反对。就在前一天,法国政府也继意大利之后宣布了迄今最为严厉且彻底的“封禁”措施。
南希在视频中朗读了自己的长文《一种太人性的病毒》,他更加肯定地宣称,“作为一种瘟疫,冠状病毒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全球化的产物”。各个国家的“例外状态”必须结合人类的整体处境来看,否则就只会让人陷入阴谋论的狂想。
“生命”和“政治”两者都呈现出自身的复杂性,令人难以掌控,这使得谈论“生命政治”显得非常“可笑”。
危险并非来自于某种外在的权力技术,因为新冠病毒揭示了问题的源头出在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食物品质和环境的有毒性”。借用尼采的说法,这些内在于我们的危险并非超越于人性,而是“太过”人性。
因为疫情,欧洲哲学家们吵翻了!
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法国哲学家,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
尽管如此,“生命政治”学说还是为哲学界广泛接受。比如,德国韩裔哲学家韩炳哲在3月23日刊载于德国《世界报》的文章中,就仍然积极使用阿甘本的“例外状态”来分析疫情。
然而,韩炳哲提醒我们,关闭边境的主权模式已经过时,政府对信息的全面掌控更需要我们警惕。
“我们是否值得拯救?代价是什么?”
3月24日,法国《世界报》刊登了与处在风暴中心的阿甘本的访谈。这篇访谈给持续了近一个月的哲学论战画上了象征的句号。
阿甘本说,作为一个哲学家,他从未想要介入科学界之间关于流行病的讨论。他感兴趣的是这场疾病所造成的伦理与政治上的极其严重的后果。
他想要强调,所谓的“例外状态”早已成为一种常态,人们在已习惯于生活在一种永久危机的状态。而现行的紧急措施的主要依据是认为“敌人来自于外部”而不是“敌人来自于内部”,没有什么比这种观念更能破坏人类的团结。
阿甘本之所以是令人尊敬的哲学家,是因为他提出了有价值的问题。印度哲学家沙吉·莫汉与迪维亚·德维迪将这个问题表述为“我们是否值得拯救?代价是什么?”

(阿甘本接受《世界报》采访时表示到:他从未想要介入科学界之间关于流行病的讨论,他感兴趣的是这场疾病所造成的伦理与政治上的极其严重的后果)
在某种程度上,阿甘本是对的。他指出了封闭的民族国家在应对疫情上的局限。因为此前,意大利和法国最为果断的措施是对外锁国,却无力处理内部的混乱。
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26日的文章也揭示了欧洲国家在应对疫情上表现出来的矛盾:“各国试图在地方层面控制病毒扩散……而瘟疫却是跨地区的”。现实很快就证明了,面对全球性的疫情,欧洲并不是一个可靠的避难所。
但是阿甘本毕竟提供了一条糟糕的出路。他一贯主张的“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放在疫情之下的确显得太不合时宜。不过,我们不应怪罪老阿甘本,甚至也不应当指望任何一位哲学家给我们最终的答案,因为哲学上的所有问题都是朝向历史敞开的。
阿甘本的“老朋友”、让-吕克·南希也已经80岁了。他回忆起近30年前,医生认为他需要安装一个心脏支架,而阿甘本则是极少数建议他不要听医生的人之一。“如果我听从他的建议,我可能那时很快就死了。”
南希则想要表达他对“老朋友”的宽容,毕竟“谁都可能犯错”。至少“老朋友”的敏锐和热心是当作“例外”来看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