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
导读:我们在“问”中亲密着彼此的关联,也在“问”中表达着迂回的情感伏线,是诗性的春花秋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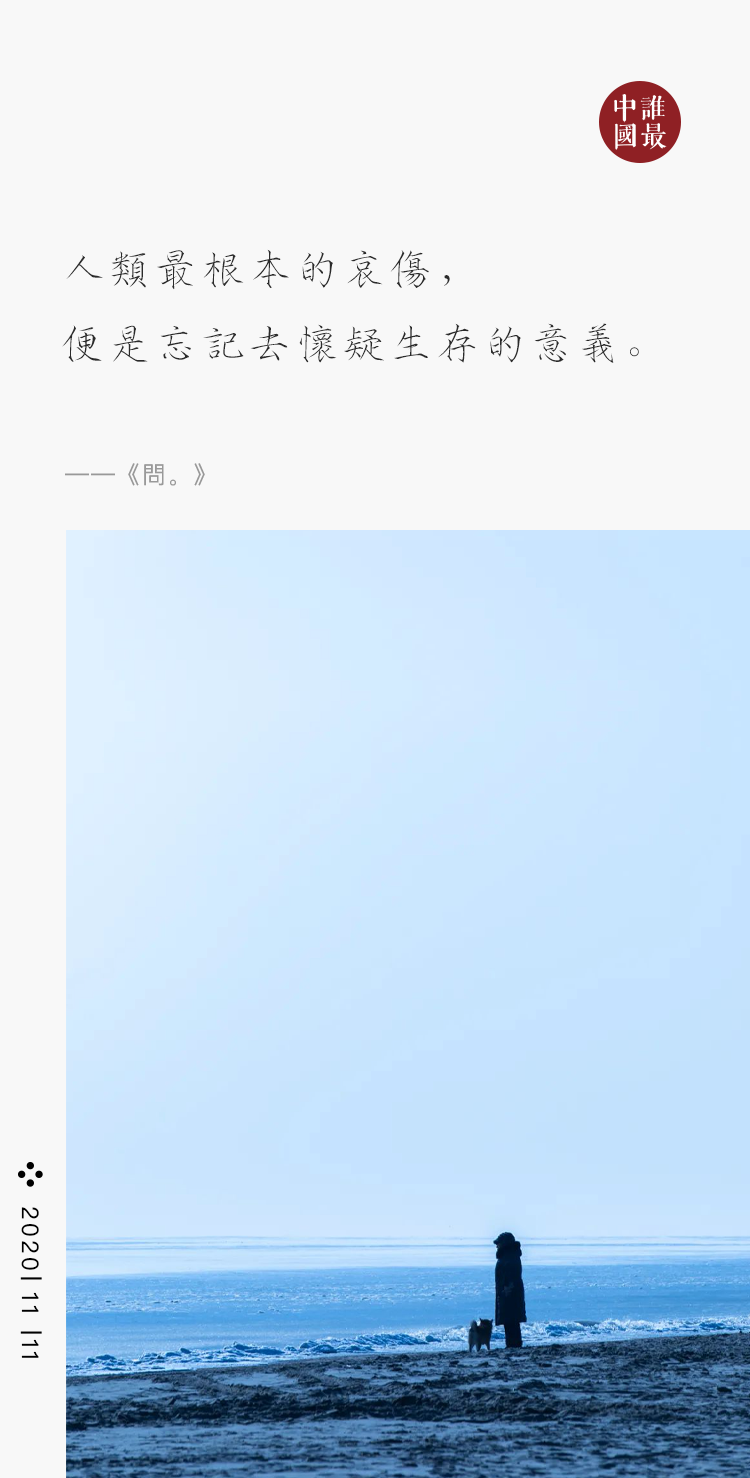
西方有句话说,“一切的伟大,均源于好奇。”
或许,好奇的伟大就在于对未知的不断发问,未知转化为有知,知识便这么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无需形而上,无需虚无缥缈。
又或许,好奇的伟大还在于对已知的发问。已知转化为无知,思维就这么螺旋上升,认知与感知的边界不间断打破着、拓展着。
问,其实当它存在时,答案已悄悄降临……


相比“问”,更多时候我们喜欢答案。
找了考卷的答案,就会有满意的分数;找到了工作的答案,就会有事业的褒奖;找到了情感的答案,就会有日常的安心……答案是稳定的源泉,提问是不安的起点。
只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答案也变得索然无味,甚至捆绑了我们。看一本书,消化完提炼出来的干货,这本书就看饱了;看一部电影,5分钟听完精彩讲解,这部电影就算看过了;写一篇文章,戳中大众痛点,总结出10万+套路,这篇文章就算成功了。“答案”,来得越来越快,人却越来越困惑了,人越困惑,就越想要找答案来填补恐惧,真是一个莫名的死循环。
这时,何不回到“问”本身,耐心觉察那恐惧的原点、情绪的前奏、好奇的伊始。

知,是在发问中一点一点生成的,灵动而鲜活。
咿咿呀呀刚学说话的孩童,好奇不知名的事物,对着父母发问,“这是什么?”于是他学会了语言,认识了花鸟虫草;有人仰望星空,发问宇宙的奥秘,于是有了天文学、物理学;有人好奇物种起源,发问人类的出现是不是偶然,于是有了生物学与哲学;有人好奇自身的感受,发问为什么快乐不起来?于是有了心理学与伦理学……
然而,当好奇心退后时,人就开始懒惰了,知识成了固态标准,拿来即用。“问”被无情略过,知识沦为工具性的,有时时被淘汰的危险。

记得以前学校里有位受人敬仰的老教授,师从皆是陈寅恪、刘文典等大家。这位老教授讲课亦精彩绝伦,有学生建议他写本书。他只是说,“我现在停不下来,因为我的思想还在奔流。”老先生七十多还带学生,对他们说,“你们别看我七十岁,我的思想比二十岁的人还新呢。”
老教授到人生的最后也没有写一本书,他去世后把自己的书捐给了学校图书馆。那些书从东方到西方,从生物到文学,从天文到艺术……他的一生都在好奇之中,一生都在发问中,所学时时在更新,无法沉淀为一本书,但在讲课中满溢的思想花火,远远比书更精彩。
毕业之后,每每想起老教授的书,就不再惧怕“问题”了。发问,时时刻刻将状态调试到好奇的状态之下,新知不断生成。人的高贵之处,不就是今日之我较之昨日之我有长进吗?不就是思想在奔流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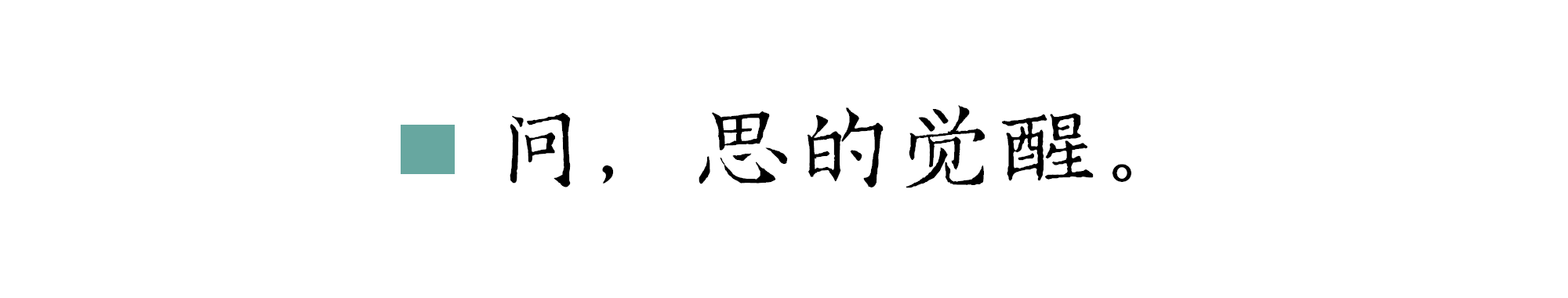
“问”归还到自己,则是拓宽自身边界的一种方式。
大思想家梁漱溟从未想过自己会走上做学问的道路,他只不过喜欢提问题,从十四岁开始问题占据在他的心间,一个问题转入另一个问题,不断解答不断又生出新的问题,解答不完欲罢不能,就一路走出了大学问。
霍金亦如此,就对宇宙的奥秘好奇,在他的脑海里,一生都在宇宙中旅行,尽管他知道,这场旅行没有终点。

梁漱溟
“问”交错在自己之外,则是与他人在交换感知的边界。
庄子与惠子的““濠梁之辩”,在子非鱼、子非我、我非子的提问中体察认知与审美的边界,鱼的快乐早已不是问题本身了。

”问“回荡在社会中,则是时代前行的能量。山本耀司说,“人类最根本的哀伤,便是忘记去怀疑生存的意义。”怀疑生存意义,简直像给生活“找茬”。有人觉得当前生活过得不错,为什么还要去怀疑?有人觉得怀疑了也没有答案,为什么要陷入无尽的苦恼?问,尚未察觉;问,察觉却已麻木。
前几年有位艺术家持续性拍留守儿童与打工父母,中间用几张火车票编织出“家”的形状。其中不乏一些面带笑容的孩子,我问这位艺术家,“如果他们感到快乐,你还要带领他们发问父母、发问社会吗?”这位艺术家很坚决,她说一定要发问。孩子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为什么要让父母缺席?为什么不告诉他们生活有别处?为什么要让他们看到外面的世界后心理承受巨大的落差?
于这位艺术家而言,重要的也不是艺术,而是一种对原生家庭的反思、一种为千千万万相同经历者的发声、一种人道精神的传达、一种能做多少做多少的笃定。

向承美 农民志 全家福 选作(来自艺术家自述:右边的女人是我小学同学。她和老公都在工地上打工,住工棚。女儿一岁时,夫妻俩就出去打工了。回万州要坐27个小时的火车,5年他们和女儿才见4面。)

向承美 农民志 全家福 选作(来自艺术家自述:这个孩子只有奶奶了,右边是空白。他爸爸在工地上干活时死了,妈妈离开再没有回来。我问他几年级,几岁,任何问题他都不回答,后来他奶奶说,站起来给阿姨拍个照,他才终于拍了这个照片。)
问,是需要察觉的,更需要察觉后的不麻木。
它是对世界保持清醒的一种思考,指向着这个世界可以更好。


有人说,中国人一切都处于提问之中。
是的,我们见面打招呼的方式是”吃了吗?”“你去哪儿?”逢年过节相互之间的关心亦是“你家今晚吃了写什么?”年轻一代总嫌这样的话多余,甚至是“刻意”。但如果把这些询问,换做陈述句的“你好”,又或是点头微笑,我们原有生活的热气腾腾就会冷却很多。
问,无形成了一种情感串联。


“问”的语气是波浪状的,节制而委婉,更富有想象空间与商量余地,与东方文化深处的韵味悠长不谋而和。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问,既是怡然的自得,又是纯净的邀请;“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的问,既是难以排遣的无奈,又是难以言喻的物是人非之感;“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的问,既是千古的喟叹,又是率性的敬仰……古典文化中的问,真真是言有尽而意无穷。
我们在“问”中亲密着彼此的关联,也在“问”中表达着迂回的情感伏线,是诗性的春花秋雨……

辛波斯卡的《万物静默如谜》里有几个迷人的短句:当我说“未来”这个词,第一音发出即成过去。当我说“寂静”这个词,我打破了它。当我说“无”这个词,我在无中生有。
“问”这个字远远比这些词更迷人,当我试图描述出它的形状时,它早已在打破自己的形状;当我试图给它个答案时,它早已转化成为另一个问题;当我还在为它烦恼时,它似乎又给我指出了一个方向……
问而学,有了学问与观念。
问而答,有了文明与启蒙。
问而思,有了回首与前行。
问而情,有了温情与深情。
匆匆若旅,别太赶路,偶尔停下来,问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