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我把周其仁的这四个字,放在脑袋里想了半年
导读:水大鱼大,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并不仅仅是量的变化。如果这个十年,中国经济发展规模扩大了一点,或者企业规模扩大了一点,那只是仅仅是正在发生的事实的一部分。我觉得水大鱼大真正呈现出来的,是水本身和鱼本身对壮大所带来的不适感。
“对于过往的十年,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您的答案是什么?”
2017 年4月,在杭州举办的一场“互联网+”峰会上,吴老师问了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老师一个问题。而他的回答只用了四个字——“水大鱼大”。
吴老师把这个词放在脑子里,想了整整半年,最后,用这个词作为了新书《激荡十年,水大鱼大》的书名。
昨天,吴老师和周其仁老师再度相遇,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36期“北大国发院博士论坛”上,进行了演讲和对谈。
01
“这本新书,我写得哆哆嗦嗦、战战兢兢的”
我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觉得那是充满诗意的三十年,指的是破坏本身具有强大的道德性和正义性。
记得90年代,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去温州第一个农民城做访问调查,那时候大概有两千多户人家住在里面,做什么呢?做铜火锅。那是中国最大的铜火锅的集散地,但干这些事,都是违法的。
后来有个老板跟我讲了一句话:吴记者,一切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你看我这儿经济很发达,发展了产业经济,所以你要支持我。后来我回去就把它写成报道,朱总理有一个批示,还专门去探讨这件事。
这样一个故事放在前三十年,可以说比比皆是。我们整个三十年的变革,是对计划经济不断突破的过程。它充满了创世纪的特征,你看着会非常热血沸腾。但是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讲,那也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创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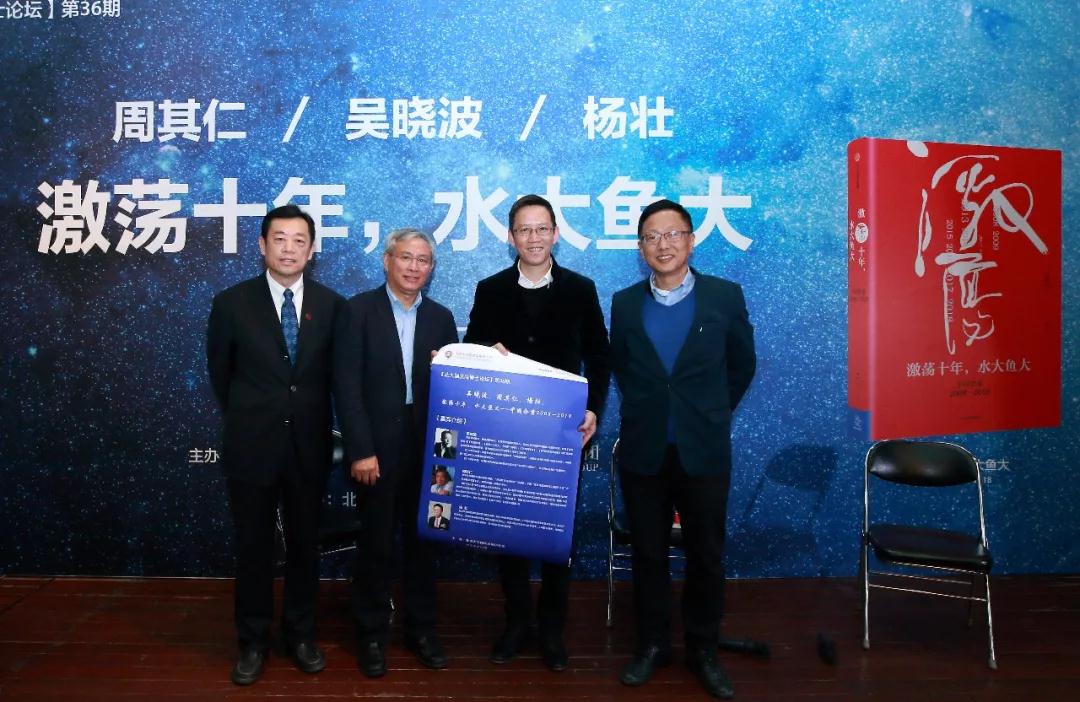
今年写激荡十年,我真觉得内心没有那么多的快意江湖。
写这本书最大的感慨,第一就是写得哆哆嗦嗦、战战兢兢。因为该讲的、不该讲的都不知道,不知道边界在什么地方。第二,这个十年所发生的很多景象非常陌生。
我写这些互联网公司,我跟这些互联网公司都很熟,每一家都去过,有一些交集了很久。我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觉得这些互联网公司的年轻人都是我的同龄人。他们当中年纪最大的是马云,1964年出生;年纪最轻的是马化腾,1971年的,比我小三岁。大概都是1964到1974年这一波的人,是今天中国商业界非常重要的人物。
我今天看他们的一些角度和我十年前看他们的角度,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当年他们是突破垄断、旧体制最主要的力量,今天他们可能已经成为垄断的一个部分了,这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这个十年,民营企业的高速发展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性事件了。相对来讲,国有企业处在相对保守的一个状态。外资企业在这十年里面,它已经慢慢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很难找到一些特别重要的影响中国产业经济的一些案例和戏剧性事件、人物或者公司。因为整个局面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法治变成了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公共事件轴。但是这一部分,我并不认为这十年来得到了特别大的进步,甚至这个十年来,我们的思想市场本身其实也并没有得到太大的开放。
企业家阶层的崛起,是中国的民营企业的崛起,他们的财富的暴涨是众所周知的全球性的重要性事件。但是在中国公民社会中,他们对应该扮演的角色和自我认知的徘徊和彷徨,反倒变成了这个十年非常重要的一个景象,甚至成为了讨论的一个禁区。
02
“中国经济发展令人感到压迫和不适”
水大鱼大,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并不仅仅是量的变化。如果这个十年,中国经济发展规模扩大了一点,或者企业规模扩大了一点,那只是仅仅是正在发生的事实的一部分。我觉得水大鱼大真正呈现出来的,是水本身和鱼本身对壮大所带来的不适感。
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和数据,是这十年来关于中国经济的一些基本性数据:经济总量增加了2.3倍,人民币规模总量增加了3.26倍,外汇储备增加了1.5倍,汽车销量增加3倍。电子商务在社会零售总额占比增加了13倍。世界500强中国公司数量从33家增加到115家。高铁里程增长138倍。
北京变得越来越有钱了,我向胡润求证了这个数据,10亿美元富豪第一是北京,第二是纽约,第三是伦敦,前六名有三个是中国的。中国奢侈品消费占全球总量70%,摩天大楼中国占了7座,深圳房价涨了4.7倍,移动支付交易额是美国的50倍,从Copy to China到Copy from China,阿里和腾讯交替成为亚洲最大市值的公司。广东经济总量相当于俄罗斯,上海经济总量相当于泰国。

这是数据上的变化,在这个规模几何级变大的同时,我认为中国对自身发展到今天所呈现的景象,充满了很大的疑惑。甚至中国经济发展对周边国家所带来的压迫性,也非常大。
我上个礼拜在东京大学做一个活动,来了大概五六百个日本人。我很坦率地跟他们讲,十年前我们来日本的时候,日本人问我们最多的问题是:我们能够帮助你们什么?我这次去的时候,日本人问的最多的是:你们还会来我们这儿买多少马桶盖呢?
这就好像一个北京大院里两个孩子,从小一起长大,小时候你还骑在我脖子上尿过一泡尿,突然一下我变成马云了,你就很难受,中国突然间变得规模扩大。周边国家都不适应我们的状况。

其实中国人对这十年的变化也并不是很适应。中国自己的公司变得强大起来了。这些公司,他们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做基础设施,已经变成了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其实我们在《激荡三十年》里看到,民营企业家冲击的、所要抗争的就是基础设施公司。你通过垄断获得很大的利益,而且这种垄断可能是行政所带来的手段。
但是今天出现了新的垄断景象,是通过市场造成新的垄断。这种垄断在全球也就中国和美国有。而这种垄断我认为到今天,可能在学理上,在法治上,都没有被认真地进行讨论。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在写这本书中,我认为我们看到的问题点。
03
“制度是可逆的,但技术变革是不可逆的”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中国40年的经济发展,它一定不是一个偶然性事件,也不是完全的西方经济理论在这个国家的拷贝,它一定有它自己的内在逻辑和动力存在。

而我的看法是,它由四部分构成。
第一,制度创新。中国从第一天起,从联产承包制、土地改革开始,我们就进行了制度创新。这些创新很大程度上带有中国特色,带有妥协性。我们的改革一定是在制度层面上进行了非常大规模的变革。
第二,容忍了非均衡。我们整个发展是从告别集体主义,告别平均主义,告别大锅饭,直接把这个桌子掀翻了开始搞起的改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或者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或者我们通过搞开发区,搞自贸区,搞自由港,通过各种各样容忍非均衡的方式,让这个国家恢复了市场竞争的内在活力,让老百姓恢复对幸福生活追求的动力。
第三,规模效应,特别是互联网和制造业这两大产业在中国的形成。中国制造业在世界排名第一,还有互联网所形成的红利,我们这些人都是移动互联网时代重要的既得利益者。这是一个庞大的内需消费崛起所带来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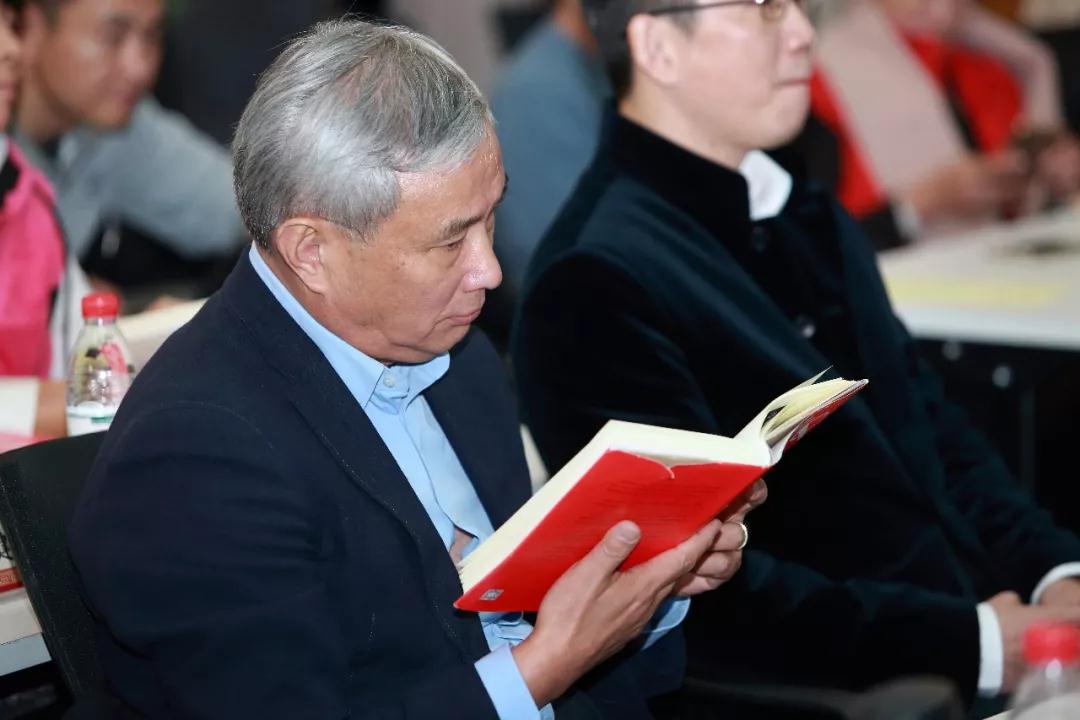
第四,技术破壁。我们在40年的发展过程中,民营企业有一句话,上面有天花板,改革是旋转门,又绕回来了。但是你会发觉说,虽然有天花板,虽然有旋转门,但是你这30年还是在不断地发展,不断地进步。为什么呢?有两个东西,制度,制度还是很重要的。
制度是人设计的,制度是可逆的。但是有一个东西是不可逆的,就是技术变革,技术变革是不可逆的。
今天,互联网进中国已经20多年了,移动互联网技术化的革命,造成了多少新的变革的可能性。但是到今天很可能移动互联网这一块,它所能够推动的技术变革的力量,我认为已经到终点了。但是我们看到新的技术变革的发生,像人工智能、新材料,我们仍然看到了中国企业和中国民营资本集团非常充满野心的探索,这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往前推进的重要力量。

《激荡十年,水大鱼大》写到最后,我选了维特根斯坦一句话:一个作者写一本书,其实跟一个女人生孩子有的时候很像,有的时候不像。对一个女生来讲,她生完一个孩子以后,孩子跟她形成了一种血肉关系,她愿意为孩子付出生命。
而一个作者跟这本书的关系要淡泊的多。这本书写完之后,你面对它,其实会变得越来越远,这本书就被放回去了。
我写了那么多书,可能十年后你再也不会记得它了。或者它在某一个时间点所呈现的一种价值观,对这个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力,到20年30年后,它会变成一种反动的力量。
每一本书都有它的命运,这种一本书所自带的魅力性,可能对一个写作者来讲,都是特别好奇的一件事情。但是今天,我完成了我的承诺。

现场对谈
杨壮:这些年的制度变化的过程之中,哪些东西我们应该继续更加深入地走下去,让我们企业家精神可以得到弘扬?
周其仁:企业也在变化,体制环境也在变化。我多少年前写过一个东西,我看在中国做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最重要的就这两条: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这山望着那山高。
第一条就是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你1983年就是做1983年的事,什么时候可以做,做到什么程度,如果你没有那个胆略,你说这个不行这个不行,那就不要叫企业家了。你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要把这个时代允许你做的空间用到尽头,这些成功的人都是有这个特点。

还有一条,你要知道中国在变化,一定要有个提前量。这个事今天干可以,过几年可能大家就看不起你,再过几年法律就说你违规的。但是我看能活下来的,他都有这个本事。
吴晓波:我认为周老师这句话非常有哲理: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对企业的定义里面讲一条,企业实际上是跟环境博弈的过程。你当时的环境特质到底是什么环境特质。如果你的企业,包括企业载体里面的企业家,跟当时的环境完完全全不合拍,你的失败的概率会很大。而且你可能在一个发生变化的环境,永远不改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