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绩效主义万岁
导读:当雷军在 2017 年的年会上,为小米定下千亿“小目标”的时候,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位反叛者的皈依。
当雷军在 2017 年的年会上,为小米定下千亿“小目标”的时候,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位反叛者的皈依。
文/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1
雷军在变,是变好还是变坏,仁者见仁。
2016 年的小米年会上,雷军说,“年初,我们定了一个 8000 万台的销售预期,不知不觉我们把预期当成了任务。我们所有的工作,都不自觉地围绕这个任务来展开,每天都在想怎么完成。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的动作变形了,每个人脸上都一点一点失去了笑容。”
于是,雷军提出,“所以我们定下了 2016 年最重要的战略:开心就好。我们决定继续坚持‘去 KPI ’的战略,放下包袱、解掉绳索,开开心心地做事。”
2016 年,眨眼既逝。
在 2017 年的年会上,过得并不太开心的雷军画风大变,他说,“天上不会掉馅饼,撸起袖子加油干。”当一个人撸起袖子的时候,一定不可能面带微笑,更不可能只是“开心就好”。

雷军为小米定了一个小目标,它被定格在一幅如天空般辽阔的大屏幕上:“小米整体收入破千亿元。”
千亿就是 KPI,KPI 就是绩效。
你在,或不在,它都在这里。
2
“绩效管理”这个概念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由美国管理学家奥布里·丹尼尔斯提出的。而早在 1954 年,彼得·德鲁克就提出了“目标管理”,在他看来,“绩效管理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在德鲁克和丹尼尔斯的理论框架中,绩效管理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它把员工绩效和组织绩效相结合,将绩效管理提升到战略管理层面。 KPI 衡量重点经营活动,不反映所有操作过程,有利于公司战略目标实现。
也就是说,绩效管理是一个只重结果,而开放执行过程的目标治理模式。
整个 20 世纪的下半叶,是绩效主义的繁荣时期,所有企业英雄都是绩效达人。曾被公认为“世界第一经理人”的通用电气前 CEO 杰克·韦尔奇,在自传中就清晰地写道:“如果说,在我奉行的价值观里,要找出一个真正对企业经营成功有推动力的,那就是有鉴别力的考评,也就是绩效考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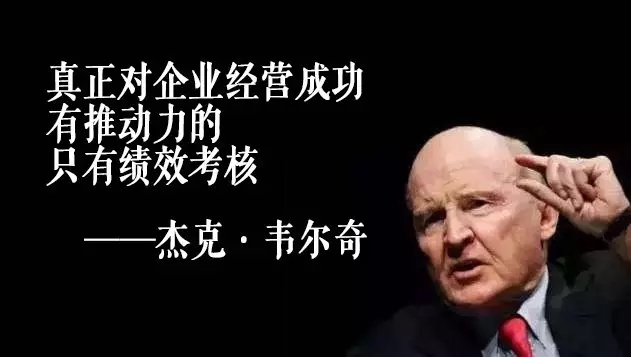
对绩效主义的反动,是从一个绩效的失败者开始的。
2006 年,索尼前常务董事天外伺郎发表了一篇文章《绩效主义毁了索尼》,在他看来,索尼引入美国式的绩效主义,扼杀了企业的创新精神,最终导致索尼在数字时代的失败。
在上世纪 80-90 年代,索尼因半导体收音机和录音机的普及,实现了奇迹般的发展。但是到了 2006 年,索尼已经连续 4 年亏损,2005 年更亏损 63 亿美元。
天外伺郎将失败的根源归结于绩效主义。
——绩效改革,使索尼子公司总经理要“对投资承担责任”,这就使得他们不愿意投资风险大但是对未来很重要的技术和产品,而更愿意做那些能够立竿见影又没有多大风险的事情。
——绩效制度的引进让每个业务单元都变成独立核算经营公司,当需要为其他业务单元提供协助而对自己短期又没有好处的时候,大家都没有积极性提供协作。为了业绩,员工逐渐失去工作热情,在真正的工作上敷衍了事,出现了本末倒置的倾向,索尼就慢慢退化了。

天外伺郎的观点,如同在全球管理界投放了一枚震撼弹,它几乎摧毁了制造业者的价值观基石。
3
任何名词一旦被缀之以“主义”,便镶嵌上了意识形态的意味,从而具备了强烈的排他性。
二十世纪的一百年,无疑是管理学的一百年,从福特工作法到美国式公司治理制度,从德国车间到丰田生产线,种种管理理念及模式上的变革,推动了工业文明的繁荣。
然而,进入本世纪之后,随着互联网经济和新的风险投资模式的兴起,韦尔奇所谓的“企业经营的成功推动力”发生了变化,相比于内部管理,商业模式的创新、新技术应用以及资本经营,显然起到了更为显赫的作用。
在中国企业界,对绩效管理的扬弃便是由互联网人发动的,进而蔓延到整个实体经济领域,而这个过程又呼应于数字化转型的大潮流。如同人在遭遇挫折时会怀疑自我价值一样,一家企业在面对重大的生态型变化时,会否定既有的制度安排,在极端状态下,会否定存在的一切。

在十年后的今天,重新回望天外伺郎的观点,有三个角度可以进行认真的商榷:
其一,索尼的衰落,是绩效管理导致的结果,还是决策层战略安排的失误。
过去十年,韩国三星的崛起与索尼恰成反例,它同样执行的是美国式的绩效薪酬制度。李健熙将经营权和责任全部分配给具有专业资质的各子公司社长,只对各子公司经营层实行的是“明确经营的完全责任、赋予履职的足够权限、按照绩效奖励团队”的管理模式。在三星经验中,绩效薪酬有力地扭转了原有的僵化体制、激活分子公司经营团队,助推三星新经营转型的目的。
在亚洲地区,台湾的富士康和大陆的华为,无一不是绩效主义的忠实执行者,甚至,他们引入了更为严格的军事化管理模式,将绩效目标的实现推向极致。
其二,互联网公司的成功,是去 KPI 的胜利,还是新的绩效目标管理的结果。
无论是 Facebook 、亚马逊还是中国的 BAT ,无一不是强绩效型企业,所不同的是,它们的绩效目标并不仅仅是利润,而更是用户,用户的数量、留存率、活跃度、获客成本及客单价。
也就是说,互联网公司的绩效模型是以用户为核心而展开,而索尼、GE 等制造企业的绩效模型是以商品为核心的。
关键不是没有 KPI ,而是 KPI 的指向体发生了微妙的改变。而无论如何变化,绩效以及与绩效相关的数目字管理,仍然是企业治理的基础性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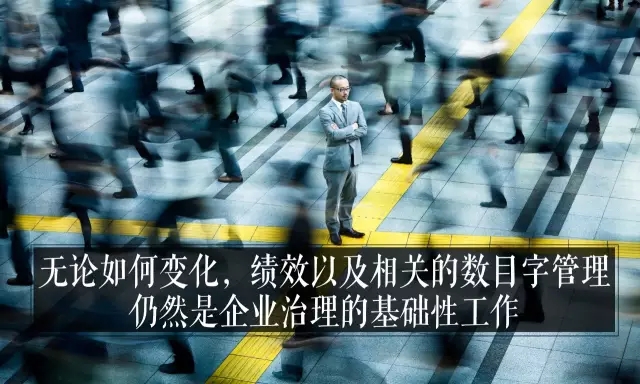
其三,索尼的总经理们“不愿意投资风险大但是对未来很重要的技术和产品”, 是绩效目标造成的,还是组织模式落后造成的。
互联网改变了信息流动的方式,进而改变了企业运营的模式和对效率的定义,这个变化对企业的组织架构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越是大型的企业遭遇的困难越大。
企业内部创新能力的激发,并不以放弃管理、特别是放弃绩效管理为代价,而是应该在组织模式上进行自我革命,形成目标高度一致、功能耗散协同、管理空前扁平、自我驱动的特种兵机制。
组织架构的变革意味着权力的放弃和重组,在进化的意义上,这是最为致命的,甚至,失败是大概率事件。这也是为什么包括诺基亚、GE 、西门子等优秀公司陷入困境的原因。
4
当雷军在 2017 年的年会上,为小米定下千亿“小目标”的时候,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位反叛者的皈依。

绩效主义的回归以及对绩效的重新解读,意味着互联网思维与新工业革命的融合,前者成为后者的基础设施。
雷军式的皈依不是回到从前,而是可能带来新的绩效管理的尝试。在管理学创新停滞了十多年之后,新的范式变革已经悄然发生,有意义的是,这一次,中国企业有可能成为最激进的实验者。